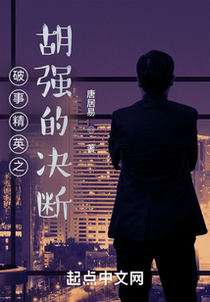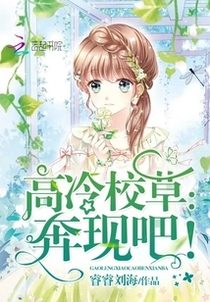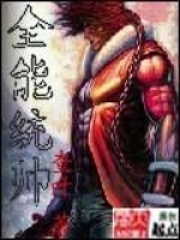第1章 活着
六月的阳光,透过出租屋那扇积着薄灰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斜斜的、有些晃眼的光斑。空气里弥漫着老房子特有的、混合了潮湿和灰尘的味道,还有楼下早点摊隐约飘来的油条香气。我坐在那张吱呀作响的二手电脑椅上,对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CAD线条图,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搞定!”我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睛,点击了保存键。这是我为客户王阿姨家老房改造设计的第三版平面图,终于达到了师傅老陈点头的标准。墙上的电子钟显示着上午10点37分,距离起床,己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肚子适时地咕噜叫了一声。我站起身,伸了个懒腰,骨头发出轻微的噼啪声。走到狭窄的厨房,熟练地拧开煤气灶,烧上一壶水。灶台旁边的小桌上,放着半袋挂面、一瓶快见底的酱油,还有一小罐猪油。这就是实习期月薪八百块支撑的日常——精打细算,但好歹能填饱肚子,还能省下一点给家里。
水开了,白色的蒸汽翻滚着。抓了一把挂面扔进去,看着面条在沸水中慢慢舒展开。我的思绪,也像这面条一样,在这间不足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在现实与对未来的模糊憧憬之间,缓缓沉浮。
我的家,在距离这个省会城市两百多公里外的一个小县城边缘。父亲朱建国,是个手艺不错的木工,几十年如一日地在各个建筑工地上挥汗如雨。他有一双布满老茧和细小伤口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常年嵌着洗不净的木屑和油泥。家里的家具,大多是父亲用工地剩下的边角料打的,结实耐用,带着一种粗粝的质朴感。母亲李秀英,是典型的农村妇女,操持着几亩薄田,农闲时就到县城的服装厂、餐馆打零工,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也把我和姐姐朱丽拉扯大。
我从小就爱琢磨。别人家的孩子玩泥巴、追跑打闹,我能蹲在父亲做活的木料堆旁,一看就是半天,看那些原本粗糙的木头如何在父亲手中变成光滑的凳子、实用的柜子。我也爱看书,什么杂七杂八的都看,脑子里总有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冒出来。可惜,这份“爱思考”似乎没能转化成优异的学业成绩。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成绩始终徘徊在中游,像一条温吞的河流,不起眼,也不干涸。父母看着我,眼里有期望,也有无奈。他们没读过多少书,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只是用最朴实的行动告诉他:读书,是走出这片土地,不用像他们这样辛苦的最好出路。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气氛有些沉闷。距离本科线差了二十多分。复读?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允许。姐姐朱丽中专毕业在工厂打工,工资微薄。父亲在工地的腰伤时好时坏,母亲常年劳累,身体也不太好。看着父母鬓角早生的白发和眉宇间化不开的疲惫,那句“我想再试一年”怎么也说不出口。
“爸,妈,”我声音有些干涩,“我……我想试试艺考,学设计?我看人家说,有些学校对这个文化分要求低点……” 这是他琢磨了很久,唯一能想到的,或许还有点兴趣,又能“曲线救国”上大学的途径。
“设计?”父亲朱建国放下手里的旱烟袋,眉头习惯性地蹙着,“那是干啥的?画画?能当饭吃?”
母亲李秀英没说话,只是用围裙擦了擦手,看着儿子。
我搜肠刮肚地解释:“不光是画画,爸。是设计东西,房子啊,家具啊,衣服啊,好多东西都要设计。学好了,也能找工作的……” 我其实心里也没底,只是模糊地觉得,这或许和我从小看父亲做木工、喜欢琢磨东西的“感觉”有点关联。
最终,是母亲拍了板:“孩子想学,就让他试试吧。总比没学上强。” 于是,家里勒紧了裤腰带。父亲多接了两个工地的活,母亲白天种田打零工,晚上还接了点缝纫的活儿。姐姐朱丽也把攒着准备买新手机的钱拿了出来。东拼西凑,终于凑够了艺考培训班和后来那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专院校设计专业的学费。
三年大专,我对此形容是“浑浑噩噩”。学校的课程理论多于实践,老师讲得也泛泛。我努力去听,去画,去学那些软件,但总觉得隔着一层什么,抓不到精髓。身边的同学,有的沉迷游戏,有的忙着恋爱,像我这样家境普通、对未来充满迷茫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往前走的,也不少。像是一叶小舟,在名为“大学”的平静湖面上随波逐流,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本能地不想沉下去。
毕业即失业,这句话在我身上应验得格外快。投出去的简历石沉大海,仅有的几个面试也因为缺乏实际经验而被婉拒。现实的冷水兜头浇下,让我从最后一点校园的温存幻想中彻底清醒。
就在我几乎要打包行李回县城,准备接受某种一眼望到头的命运时,一个偶然的机会降临了。同宿舍一个家境稍好的同学,家里在省城开了间不大不小的装修公司,正缺一个设计助理打杂。
“朱星,你不是会点CAD和3D吗?要不要来试试?工资不高,就八百,包住不包吃,但好歹是个入行的机会。”同学在电话里说。
八百块!在省城!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刻答应了。这简首是溺水之人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告别了父母担忧又带着一丝希望的目光,扛着简单的行李,一头扎进了这座繁华喧嚣、却又冰冷现实的都市丛林。
于是,我成了“星艺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的一名设计助理。说是助理,其实就是打杂跑腿的万能胶。量房时扛着沉重的激光测距仪和工具箱,跟在设计师后面记录数据;工地现场,帮着盯一下材料进场,协调工人(虽然工人大多不怎么听我这个毛头小子的);回公司,帮设计师们打印图纸、装订方案、买咖啡、点外卖;更多的时候,是对着电脑,把设计师手绘的草图或者潦草的指令,用CAD一笔一画地描绘成规范的施工图。
带我的设计师老陈,是个西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技术扎实,经验丰富,但脾气火爆,要求极其严苛。我没少挨骂。
“朱星!你这尺寸标得跟狗爬的一样!眼睛长哪了?”
“这墙能这么拆吗?承重墙!承重墙懂不懂?你想让楼塌了砸死人啊?!”
“材质标注呢?光画个框框谁知道你里面贴瓷砖还是刷乳胶漆?脑子呢?”
起初,我被骂得面红耳赤,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八百块的工资,似乎连承受这份责骂的底气都不够。下班回到那个位于城中村、阴暗潮湿的出租屋,累得倒头就睡时,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设计?做的这些琐碎、重复、毫无创造性的工作,和我想象中的“设计”相去甚远。
但我身上有股韧劲儿,像野草。这韧劲儿可能遗传自父亲那双能磨平木头棱角的手,也可能源自母亲日复一日在田间地头的默默劳作。挨骂归挨骂,委屈归委屈,我骨子里那份“爱琢磨”的劲头反而被激发了出来。开始更用心地观察。
老陈骂我尺寸标得乱,我就把公司里所有优秀案例的图纸找出来,一张张研究别人是怎么标注的,尺寸链怎么拉才清晰合理。老陈说我不懂结构,我就偷偷啃起了建筑构造和施工工艺的书,还在网上找各种教学视频,晚上回到出租屋对着电脑一点点学。量房时,不再只是机械地记录数据,开始留意房子的朝向、采光、通风,观察业主的生活习惯和潜在需求。老陈和客户沟通时,竖起耳朵听,琢磨老陈是怎么引导客户、怎么把专业术语转化成客户能听懂的话、怎么在客户天马行空的想法和现实可行性之间找到平衡点。
我变得异常勤快。设计师们需要什么资料,我总是第一个跑去找;工地现场有什么小问题,我主动去协调处理,解决不了就及时汇报;脏活累活,从不推脱。慢慢地,老陈骂我的次数少了,偶尔还会在改完他画的图后,淡淡地“嗯”一声。其他设计师也愿意支使我干点稍微带点技术含量的活了,比如让我根据要求修改一下效果图的局部,或者整理一下复杂的物料清单。
日子就在这忙碌、琐碎、偶尔有点小进步中悄然滑过。一年多的时间,省城的西季在车窗外流转,我却几乎没有时间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风景。生活轨迹就是出租屋、公司、工地,三点一线。皮肤晒黑了些,人也瘦了点,但眼神里那份初来时的迷茫和怯懦,被一种沉静的专注取代了。我依然拿着微薄的薪水,依然住在那个冬冷夏热的小屋里,但我开始感觉到,自己似乎正在触摸到“设计”这门手艺的一点点真实的脉络——它不仅仅是画漂亮的图纸,更是理解空间、理解人、理解材料与工艺,并在各种限制条件下找到最优解的复杂过程。
就在昨天,我帮老陈完全独立地完成了王阿姨家旧房改造的所有施工图深化工作,并且一次通过了老陈的审核。老陈破天荒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小子,有点样子了。王阿姨那边看了图很满意,点名要你跟现场。”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肯定!我心里像被注入了一股暖流,干劲更足了。今天一早就爬起来,把最后一点收尾工作做完。
面条煮好了,捞出来冲凉,拌了点酱油和一小勺猪油。简单的味道,却足以慰藉辘辘饥肠。一边吃着面,一边翻看着手机里存的王阿姨家的现场照片和设计图。老房子,六十多平米,格局不合理,采光差,管道老化。设计着重解决了动线、采光和收纳问题,虽然方案在老陈指导下完成,但很多细节是我反复推敲的。
正看着,手机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妈”的名字。
“喂,妈。”我咽下嘴里的面条,声音带着笑意。
“星星,吃饭没?”母亲李秀英熟悉而温暖的声音传来,背景里似乎还有父亲敲打木头的轻微声响。
“正吃着呢,妈。你和爸吃了吗?”
“吃了吃了,刚收拾完。你爸今天腰还行,在院里给你姐打个小凳子呢。”母亲的声音里透着轻松,“你那边怎么样?工作累不累?钱够不够花?别太省着,该吃就吃。”
“不累,妈。挺好的。今天刚做完一个项目,师傅还夸我了呢。”朱星报喜不报忧,“钱够用,您别操心。姐呢?”
“你姐今天调休,在家呢。刚还说给你寄了点家里晒的菜瓜和咸肉,让你尝尝家里的味道,省得老吃外头那些没营养的。”母亲絮叨着,“在外面别太拼,注意身体。家里都好,不用惦记。”
听着母亲的唠叨,看着碗里简单的面条,心里暖暖的,又有些发酸。家里的“都好”,是父母用多少辛劳换来的?姐姐在家照顾父母 ,这何尝不是对姐姐的禁锢?
“妈,我知道了。你们也注意身体,让爸别太累着腰。”朱星叮嘱道。
挂了电话,出租屋里恢复了安静。窗外的城市喧嚣被薄薄的墙壁过滤,只剩下模糊的背景音。朱星看着电脑屏幕上王阿姨家的设计图,一个念头无比清晰地浮现出来:
不能再只是“助理”了。我想要真正地“设计”。我想要像父亲打造一件完美的家具那样,亲手打造一个舒适、美好的空间。想要靠自己的本事,挣到能让父母不再那么辛苦的钱,能让姐姐不用那么省的钱。
这念头像一颗被压抑己久的种子,终于顶破了现实的硬壳,带着倔强的生命力,探出了头。
我知道,前路依然漫长且艰难。从助理到设计师,隔着的不只是经验的鸿沟,还有资历、人脉、甚至运气的重重关卡。依然渺小,依然贫穷,依然身处这座巨大城市的底层。
但这一次,不再只是被动地承受和适应。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一个想要奋力跳起来去够一够的果实。
关掉设计图,打开招聘网站,在搜索栏里,郑重地输入了两个字:“设计师”。
屏幕的光映亮了年轻却带着几分沉稳的脸庞,那双爱思考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名为“渴望”的光芒,虽然微弱,却异常坚定。都市的尘埃和霓虹交织的光影在他身后流动,属于我的“设计”之路,才刚刚在这片钢筋水泥的森林里,刻下第一道属于自己的、微不足道却充满力量的星痕。